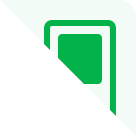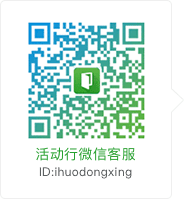

《伤心的人》新书分享会
Hide
Event DetailsHide...
很久以来,我都想写小说,但又怀疑自己讲不出故事,直到我拍了一些带有叙事性的录像,编了几个属于情景对话的短剧,才发现故事原来就隐藏在画面或概念中,写小说就是将故事从词语的深海中打捞上来。
粗略估算了一下,三十年来,我在广州以及周边乡镇租赁的物业超过了五十处,这也意味着我跟同样多的业主签订过合同,有过同样多次数的搬迁。如果每搬到一个新地方带来的兴奋都是短暂的,无尽的折腾倒是带给我能够接触到不同社会人群的好处, 这比我在学校当老师只面对同事和学生要丰富得多,当然啦,我并不是为了体验这一点才去租房子,实在是因为我对“文化实践”的理解是从办书店开始的,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多的空间实践,它们构成了我的无法倒推的人生。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好,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差。
这部小说并不是对这三十年折腾的记录,也没有写到过任何一次搬迁。在构成故事这一点上,里面出现的人物和情节也不是我长期接触的人和亲身经历的事,如果说它们算不上虚构,那么它们就属于现实主义创作中所谓的“典型”,是将广泛的社会生活放进一个处理器进行蒸发之后得到的结果。我相信任何有经验的作者都会同意这一点,我之所以强调它,只是想交代一下这部小说的来历:它没有在写作大纲的规划下一步步深入生活展开调研,也没有受到某个具体事件的刺激,它的形成———从人物到情节———都是源于一个录像,而录像又源于书店,源于书店所处的具体社会。如果说书店一直都处于社会的包围当中,起初是校园,后来是商业大楼,那么只有到了昌兴街,它才真正被安插到广州的城市生活中,以一种失败者的姿态暴露在各类人群的眼前。
尽管昌兴街是一条短而直的小巷,但它也像一幅卷轴风俗画,立于其中的书店可以成为市井生活的观察哨和舞台,就像老舍的《茶馆》一样。更为贴切的想象可能是电影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和电视连续剧《外来媳妇本地郎》。如果说我并没有抄袭它们,但的确得承认某种意义上我在向它们致敬,也就是不由自主地建立起了小说和它们之间的互文性。当然啦,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,我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积累都有那么点自以为是,或者说还停留在作为画家的可怜的形式表面,但愿这一不足还能从“间离效果”上找到理论支持。
如果说小说从来没有真正的虚构,那么我笔下可能有的真实性都是来自我自己,我是人物的替身和影子,我既是野山,也是谭明珠、丁先生、肥佬和阿六、阿七,我是所有的人和物,甚至那些真实的街道名字,也是因为我对它们比导航还熟悉。在这里,我再一次向你兜售福楼拜著名的“包法利夫人是我”,它对我来说,如今已成为医治想象力匮乏的万金油,坚如磐石的文学立场,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拉不开距离,为什么不同的人物总是用相同的语气说话。看着这些替身和影子,想想故事所隐含的主题,我也时常会感动一番,那也许是因为我作为可能的他们,某些方面恰恰是被这长时间的折腾给遮蔽或覆盖了,而写作就是一次清理和暴露。
每个人都有过伤心的一天,无论是爱情失落还是时光不再,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未知或改变都可以带动伤心的情绪。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尽量让它们看上去结实可靠,同时又真正地保护那些不可能说清楚的模糊。
C. T.
PS: 不要忘了我是画画的,擅长用相同的手法表现不同的事物,一下笔就带有自己的气息,穿上不同的衣服就成了别人。你看到那些人总是能想起我,这一点也不奇怪,我甚至觉得“千人一面”的评价对画家是一种赞扬。
Event Tags
Recently Participation
-
飞翔爱情Like
(5个月前)
-
 吴十二少Register
吴十二少Register(5个月前)
-
王一Register
(5个月前)
-
 徐SirRegister
徐SirRegister(5个月前)
-
 TLNRegister
TLNRegister(5个月前)
-
明天不散步了Register
(5个月前)
Perhaps you'd be interested in
Question
All Questions
OrganizersMore

杭州单向空间

单向空间是集实体文化空间、全媒体原创内容出版、文化沙龙、文创礼品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机构。 在消费和娱乐统领的时代,单向空间始终强调思考的价值,汇聚我们时代最有力量的思想者和创造者,分享经验,表达洞见,树立榜样,为人文精神赋能,为创造力欢呼,引领年轻一代拥抱智性生活方式,过更有意义的生活。 2005年,许知远、于威、张帆等几个年轻媒体人在圆明园的一座院落里创办了“單向街图书馆”,名字取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同名著作《单向街》。2014年,品牌更名为“单向空间”,同时也走出北京,相继在阿那亚、杭州、上海等多地开设实体空间。整个品牌也升级为包含书店、线上媒体、音视频节目、文创产品、IP活动、咖啡餐饮、出版业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创意机构。 单向空间旗下子品牌包含:单读(全媒体出版品牌)、十三邀(精品人文视频栏目)、OWSPACE(精品文化生活用品品牌)、单向咖啡、十三邀小酒馆、单向街书店文学节、单向街书店文学奖、单向历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