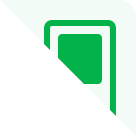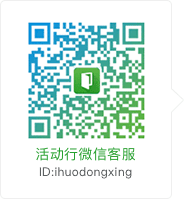

未被摧毁的一次分神——《始于一次分神》品读分享会 | 思南经典诵读会第166期
Hide
Event DetailsHide...

11/05 思南经典诵读会 未被摧毁的一次分神 品读《始于一次分神》 如何在一本书中同时窥见辛波斯卡、米兰•昆德拉、略萨、马内阿、特雷弗、君特•格拉斯、鲁西迪、里尔克、帕慕克、阿兰达蒂•洛伊等著名的中外当代作家?在胡桑的新书《始于一次分神》当中,他以诗人的敏锐、学者的严谨对上述作者进行了细读。 《始于一次分神》收入了胡桑从2010年至2018年间创作的书评,指向文学构筑潜能生活的能力。在写作中,胡桑秉承了纳博科夫《文学讲稿》的细读方法,深入文本肌理,揭示文本写作的秘密,为读者开辟出诸多通往文学作品的条条幽径。通过胡桑的解读,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目击一个充满差异和竞争、最终能够和解的完整精神世界。 胡桑的书评在文本与现实、历史与想象、形式与价值之间游刃有余地自由穿梭,文字摇曳动人,又处处引领着读者去沉思文学、生活与生命之间的幽谧联系。这不仅仅是一本书评集,同时也是一本探讨文学何为的思想论集。 11月5日(周五)晚,诗人胡桑、评论家李伟长将来到思南书局,与读者共读书评集《始于一次分神》,延拓创作背后的所思所感。 时间:2021年11月5日 19:00-21:00 地点:思南书局 嘉宾:胡桑、李伟长 嘉宾简介 胡桑,诗人、译者、学者,著诗集《赋形者》、评论集《隔渊望着人们》《始于一次分神》,译有洛威尔、奥登、辛波斯卡等人诗集和随笔集,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。 李伟长,供职上海文艺出版社,写评论和阅读随笔,著有《珀金斯的帽子》《人世间多是辜负》《未被摧毁的生活》。


诵读篇目:
一、《大海,全是水,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》(代序) (第21-24页)
•说到底,任何自我都无法彻底成为他者,只是在与他者的交往中,叠加了他者的影子,成为随行着复数影子的自我。在趋向中心的翻译中,巴黎没有成为罗马,纽约没有成为巴黎,北京也没有成为纽约。翻译,应该是一个敞开、变形、转化的过程,甚至是一个消解中心的过程,一切源于一门语言及其文明试图理解自己、成为自己的欲念。翻译的深处有着试图在变形中寻求可能生活从而与生活和解的愿望。
•翻译,让母语流动起来,逡巡于边界而生机盎然。流动的开阔的存在才能承受盈余的事物。正如莎士比亚在第135首十四行诗中写的:“大海,全是水,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。”而清浅的池塘或细小的河流会在暴雨中决堤。海洋在接纳中释放,在释放中接纳。
•话说回来,为什么我当年不喜欢书写江南乡村和城镇的生活?因为我觉得那份生活太切身了,是窒息着我的日常生活,并不能提供我对世界别样的想象?其实,主要不是江南城镇和乡村生活的贫乏,而是我当时的理解力的孱弱,理解力的孱弱又源于语言的迟钝和表达的凝固。我缺少倾听和观看,尤其缺少阅读,因而没有能力去理解江南小镇的当下生活之中隐藏着的可能的形式。因此,就一味想着越界和逃离。
•多年后,我遇见了但丁在《地狱篇》第二歌里的句子:“人海波澜,不下于大洋的狂风怒涛呀!”(王维克译)许许多多的人有着惊人的波澜。我终于发现,我渴望波澜和狂风怒涛,渴望置身于他人的波澜,从而安放躁动不安的自己。那么,倘若我是死水一潭,怎能呼应他人的波澜,承受他人的风涛?
二、《大海,全是水,仍然把雨承受下来》(代序) (第23-24页)
•那么,写作,之于我,到底是什么?写作只是如实写下自己经历了的生活?还是去重新构造自己、改变自己?或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生活着当下的生活?
•胡桑是我的笔名,谐音于湖桑,后者是我老家湖州的一个桑树品种。家里的房子后面生长着一大片浩瀚的桑树林。我曾经一直漫游其中。我在大学时开始使用这个笔名,漫游在异乡,我却与自己的故乡和解了。我不想只生活在原名里。笔名是生活的增补和溢出。这种方式类似于写作。写作始于一次分神、忘我、偏移、构造。无可奈何的是,这又会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离、甚至缺失了责任的写作。但是这个笔名还有一层意思,我想要去转化当下的生活,而不是逃离。因为我保留了我的姓,这是我与亲人、生活、故乡、土地的联系。
•大卫·格罗斯曼(David Grossman)曾在一个访谈中说过:“写作是我理解人生的一种好方式。只有写作,我才能理解人生。通过写作来理解自己和家人所经历的不幸。通过写作正确地了解生存境况。在写作时,很多事情变得清晰了,越写越觉得写作确实是应对失落、毁灭与生存的最好方式。”通过写作,我理解了自己和他人。那些幸运的、不幸的记忆都可以在写作里溶解而焕发出如梦似幻的氤氲,让我激动不已,又恍惚迷恋。不过,最终我收到了明亮日子的邀请。
三、《超现实的相遇》 (第32-34页)
•这就是当代艺术的命运,也是当代小说的命运。正如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拉贡所言,在当代,小说是一门“被贬低的艺术”。小说被贬低的命运与整个艺术的命运休戚相关。在这个技术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,不仅存在被遗忘,能够照亮生活世界的小说也被贬低、被驱逐。世界迎来了自己的黑夜。如何穿越这个黑夜?唯有通过与艺术的相遇,“超现实的相遇”:与日常生活的平庸性相遇,与形而上的忧虑相遇,与世界破碎之前先人的亲密生活方式相遇。具体到小说这门艺术里,是让梦与现实相遇,让拉伯雷以来的所有传统相遇。昆德拉渴望的是,世界在奇特的相遇中轻盈起飞,回归自由。
•相遇,并不是简单的并置,不是双方的妥协和苟合,也不是最终的一体化,不是对信念的幼稚忠诚,一旦相遇,双方的中间地带会产生一个奇妙的存在场域,这是一种友谊,一种“唯一的美德”。《相遇》一书的封面是两个体态生动的人伸开手臂试图拥抱对方,他们渴望一次真正的相遇。这幅漫画是昆德拉亲手创作的。在《敌意和友谊》中,昆德拉提起自己特别喜欢一张照片,那是法国诗人勒内·夏尔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拍摄于“二战”后的照片。夏尔走在海德格尔的身旁。一个因参加过反抗德国占领的抵抗运动而受赞扬,一个因曾经对纳粹主义表示认同而受到诋毁。照片上,可以看到他们的背影。他们都戴着帽子,一个高,一个矮,平静地走着。他们的并肩行走,一种“奇特的相遇”。在昆德拉看来,“相遇”是一种“友谊”。他们的中间地带是“存在”,“存在”诞生于双方的相遇,而不是敌对与割据。面对这样一张照片,也许,我们可以更好地去理解昆德拉所谓的艺术任务——“对存在的探测”。
四、《在“准”的国度》 (第64-67页)
•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辨认,会与世界的权力法则产生矛盾和错位。男人在这一冲突中,可以继续做一个任性的男孩。女人在这一冲突中,只能去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。这就是一个社会本身的非理性之处。女人,应该可以继续成为女孩,这是一个伦理性的时刻。伍尔夫笔下的女人——“达洛卫夫人”(Mrs.Dalloway)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伦理时刻。她沉浸在绵远的记忆里,不正是试图唤醒身上的女孩——“克拉丽莎”?
•一个女人,不想成为女人,拒绝成为贤妻良母,那么她应该如何去爱?阿兰·巴迪欧在《真正的生活》中区分了四种传统女性的形象——女仆(Domestique)、女妖精(Séductrice)、情人(Amoureuse)和圣女(Sainte)。女仆是家庭主妇-母亲的形象,充满了对家庭的爱。女妖精则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女人,甚至声名狼藉的女人,其更极端的形式就是妓女。母亲和妓女之间相互对立。女妖精如果远离了欲望则是情人-爱恋者。情人背负着爱情的梦幻。女妖精体现了不纯的爱情,是欲望的化身,情人则体现了纯洁的爱情,是爱情本身的化身,并且不用成为家庭主妇。爱如果更加纯粹,提升为崇高的爱,恋人就成为了圣女。
•那么,《送奶工》的叙述者并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。剩下的出路就是,要么如佩吉那样去爱上帝,成为圣女,彻底不爱男人。要么成为女妖精,将爱发展到欲望、疯狂、暴烈、畸形的状态——这恰恰就是社区对她的误解。要么成为纯粹的情人,将自己交付给爱本身,而拒绝道德规训意义上的爱,也不信任放任自流的过度的爱——叙述者与准男友之间的“准”的关系中是不是将自己塑形为了“情人-爱恋者”?在共同体看来,叙述者的“走路看书”是一个出格的疯狂行为,因此她是一个女妖精。其实,她一直在试图成为拥有纯粹的爱情的人。这是女人把握自身命运的伦理时刻,这是对健全的、理性的、权力的社会的解构,女人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,她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展开,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使用,自己决定自己精神的安放,以期获得相互解放的爱。
•一个人,尤其是女人,想要成为自己,需要去尽情释放属于自己的生命力量,而不是克制自己的生命力量——通过克制与社会的法则妥协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对于作为“中间女儿”的叙述者来说,女孩只有一种未来吗——成为妻子和母亲,贤妻良母?一个女人,应该可以成为女人也可以继续成为女孩,活在一条开放的边界上。
五、《在清晨醒来》(第223-224,245-247)
•一个人的生命是在对技艺的获得中展开的。在生命的展开中,力求完满,这是人的宿命。人人各异的能力塑造了不同的完美,这似乎也是宿命。能力,却可以在人身上获得、发展和改变,这大概是对宿命的抵抗。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开篇就说:“每种技艺和研究,同样地,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,都以某种善为目的。”他所谓的善指向人性的完满或幸福(εὐδαιμονία)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,人有三种生活:动物般的享乐生活,具有政治性的共同体生活,追寻自由的沉思生活。只是,一旦求索人性完满的技艺蜕变为单纯的知识甚至技术,人的三种生活都会变形、扭曲甚至反过来对人进行奴役,人存在于世的意义就会被悬置以至于枯竭。这么看来,在技术昌盛转而奴役人的时代,诗人转入对自然的书写,并非只是受到了田园牧歌的诱惑,而是对人的未来在进行积极的选择和想象。玛丽·奥利弗就是这样一个诗人,和弗罗斯特、加里·施耐德、露易丝·格利克一样,她是在寻求别样道路的诗人。
•奥利弗诗歌中一直有着对超验世界的敬畏。“光”对奥利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物。她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诗集,就叫做《光之屋》(House of Light)。整个屋子充满了光,也就充满了幸福,一种超验的幸福。《我为何早早醒来》第二节里追寻了“光”的超验来源:
最好的传教士,
可爱的星,正是你
在宇宙中的存在,
使我们远离永恒的黑暗,
用温暖的抚触安慰我们,
用光之手拥抱我们——
早上好,早上好,早上好。
•结尾一行具有强烈的仪式感,仿佛诗人和自然事物之间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瞥,而是犹如上帝在创世时投下的凝视。诗人接连说出三个词——“早上好”(good morning),这是朴素的日常语言,但已经脱离了日常语义,进入面对自然时的敬畏的瞬间。于是,在这个仪式之后,一天才真正开始。也许我们在尘世中受生活奴役,浑浑噩噩,操劳度日,并没有真正去开启每一天。时间的开启是精神世界的打开和醒来。我们需要在每一天清晨真正醒来,让那觉醒的风吹拂明亮的日子。让时间展开,让日子栖居在我们的生命里。正如弗罗斯特在《林间空地》中写的:哦,寂寂温和的十月清晨,
让今天的时光慢慢展开。
让今天对我们显得不那么短暂。
Event Tags
Recently Participation
-
 葡萄Register
葡萄Register(3年前)
-
 乔仔_007Like
乔仔_007Like(3年前)
-
MochaRegister
(3年前)
-
 欢乐马Like
欢乐马Like(3年前)
-
 欢乐马Register
欢乐马Register(3年前)
-
雪fufuRegister
(3年前)
Perhaps you'd be interested in
Question
All Questions
OrganizersMore

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上海世纪朵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成立的全资子公司,是推进集团“双轮驱动”发展战 略的最新业务板块。公司将在城市的商区、园区、学 区、社区打造一批集书房、讲堂、展厅、会场、文苑、客 厅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新型阅读文化空间,并以“朵 云书院”为核心品牌,快速形成门店连锁。 公司已相继开业四家门店:朵云书院广富林店、思南 书局、大世界店和舞蹈中心店,并成功举办思南书局 快闪店。